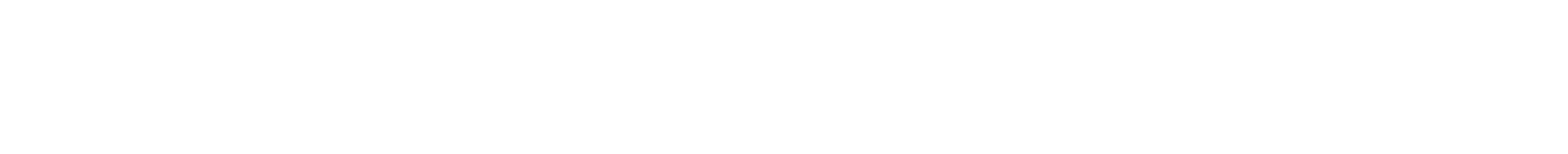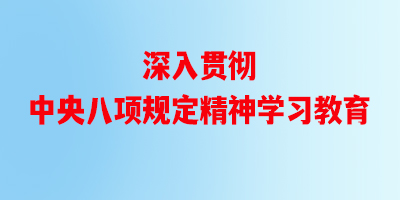记一次难忘的创作经历
编者按:2023年是《首都公共文化》创刊30周年。为纪念这本在文化馆乃至公共文化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内刊,我们策划了一系列活动,包括历史回顾、专家访谈、主题征文等。敬请关注。

作者:朱玉儿,现就职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公共文化中心,馆员,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员、门头沟区作家协会会员、门头沟区音乐家协会会员。
苦恼
“接北京市文化馆的通知,第六届创写北京2023年《首都公共文化》创刊30周年征文活动正在征稿,希望咱们馆的业务干部们都踊跃参加一下!”
坐在办公室里,我的脑海里不断回响着馆长在例会上说的话,心里很想写点什么,但却毫无头绪。
“玉儿,这回的征文活动想写点什么呀?”耿姐笑盈盈地问。
“嗯……”我苦恼地摇着头“发愁啊!姐,我刚看了看征文要求,这要是别的题目我还能有点儿想法,这次让写和《首都公共文化》的故事,专刊(编者注:专刊另有其意,此为作者惯用说法,未改动,下同)已经创办30年了,我来咱文化馆干群文工作才几年呀!看了征文上的介绍,我才知道专刊最早叫《北京大观园》,后来改成《群文博览》,到2012年才更名为现在的《首都公共文化》。一路走来它记录了多少三十年间群文界发生的大事、推出了多少优秀的群文作品啊,就我来这几年,还经历了一次改版。《首都公共文化》这三十年岁月的厚重,我真真儿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呀!”
“玉儿,不了解,可以去想办法了解了解嘛!”红姐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,递给我一本最新的《首都公共文化》“来,看看书,找找灵感,你来这几年不也在上面发表过一些作品嘛!这不也是属于你跟专刊的故事和缘分嘛!你看,我之前还当过几年咱们馆《首都公共文化》专刊的通讯员呢!记得……”
“不了解,就去想办法了解了解!”翻着手中崭新的《首都公共文化》,我在心里反复琢磨着红姐的这句话,陷入了沉思。
或许,这是个办法
“2014年4月,总第17期;2016年……”我小心翼翼地拆开新到的快递,小声核对着一些编号“加上这几本,总算都收集齐了。”嘴角不禁微微上扬:“这已经是在各种购书平台上能找到的全部《首都公共文化》旧刊了,真是让人一番好找!”
“不了解就想办法去了解!”几天前红姐的话在我心里扎了根,到底该怎么去了解呢?思来想去,要了解得先有对象才行啊,既然想了解专刊的曾经,那我就得去读读以前的《首都公共文化》。通过从各大购物平台、旧书平台上进行全网搜索,终于让我找到了十二本从2012年到2018年的《首都公共文化》专刊。
嗅着旧杂志飘来的名为岁月的阵阵沉香,抚摸着这十二册《首都公共文化》专刊封面的斑驳,仅凭这十二册的旧刊物根本无法全面地展示《首都公共文化》三十年以来的辉煌,只不过是它漫长历史的冰山一角罢了。但,也许从中真的能找到解决我写作苦恼的答案。那么,从哪一本开始寻找呢?
一阵困意袭来,夜空中的星星眨着明亮的眼睛,月亮无声地穿梭于薄云间,万籁俱寂中,或许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,期待着这十二册旧杂志里有着怎样精彩的、属于群文人的世界和故事。
梦境or现实
“咚!咚咚!”一阵阵有力的鼓声伴着喝彩声、掌声传入耳中,我心想这是谁把电视打开了,伸了个懒腰,映入眼帘的是绚丽的舞台、人山人海的观众以及在舞台上尽情表演的演员。
我使劲揉了揉眼睛,随着最后一声鼓点的敲击和台上演员动作的定格,全场瞬间响起了如雷般的掌声,还没来得及看个仔细,灯光变暗,一个主持人模样的人走了上来:“欢迎回到我们2012第八届舞动北京——群众舞蹈大赛的现场,刚才是由门头沟区文化馆选送的广场舞《童子大鼓》,再次感谢我们门头沟区文化馆精彩的表演,下面请评委为他们打分。”
2012年?第八届舞动北京?仔细环顾四周,此时我好像正身处于一个巨大的体育馆内,此刻我好像正在2012年第八届舞动北京的现场?!处于震惊中的我连连后退,“哎呦……嘶……”一个没站稳坐了个结结实实的屁墩儿。原来在倒退中,我不小心摔到了一扇门的外面,只见这扇洁白的大门上赫然写着“‘十八大’专刊”五个大字。
站起身环顾四周,一个白晃晃的空间里有着许多跟刚才一样的大门,上面都有着各自的编号,如“2014—6、2018—5”等等,有的上面没有类似的纯数字编号,而是写着“试刊总第9期”的字样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?这些门后面又是什么呢?瞬间燃起的好奇心一下子取代了刚刚的惶恐和不安,怀着些许兴奋和期待的心情,我打开了编号为“2022—1”的大门。
门里面的光亮让我一刹那无法睁开双眼,唯有周围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好不热闹。这是在进行什么比赛吗?等我再次睁开双眼,只见碧蓝的天空下是一片宽阔的室外冰场,冰场上人声鼎沸,有身穿运动服、贴着号码的,像是参加比赛的选手;有穿着警察、清朝官员服装的,还有打扮成米老鼠、剑客的,唯一相同的是大家的衣服都很有年代感,而且都穿着冰鞋在滑行。“这场景,怎么有点儿眼熟啊!”我心里正疑惑,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我身后由远及近地传了过来:“这位同志,您可不能站这儿,这儿是比赛滑道,您站这儿太危险了!”
我转身看见一个身穿校服、脚踩冰刀的小姑娘朝着我快速地滑了过来,她熟练地转了个圈,便停在我的面前,上下打量我一番,调皮地说:“同志,您……您穿这身儿不冷啊!”我看看自己的一身夏装,再看看冰场和她说话呼出的白气,突然想起了什么:“同学,你叫什么呀?”
“我叫郝晴,今儿代表我们学校来参加北平冰上运动会!”
郝晴?这不是我之前写的小说《滑出一个梦》里的人物嘛!这难道……我记得这篇小说刊登在《首都公共文化》专刊2022年第一期里,2022年第一期,2022—1?刚好是这扇门的编号!一瞬间我好像明白了什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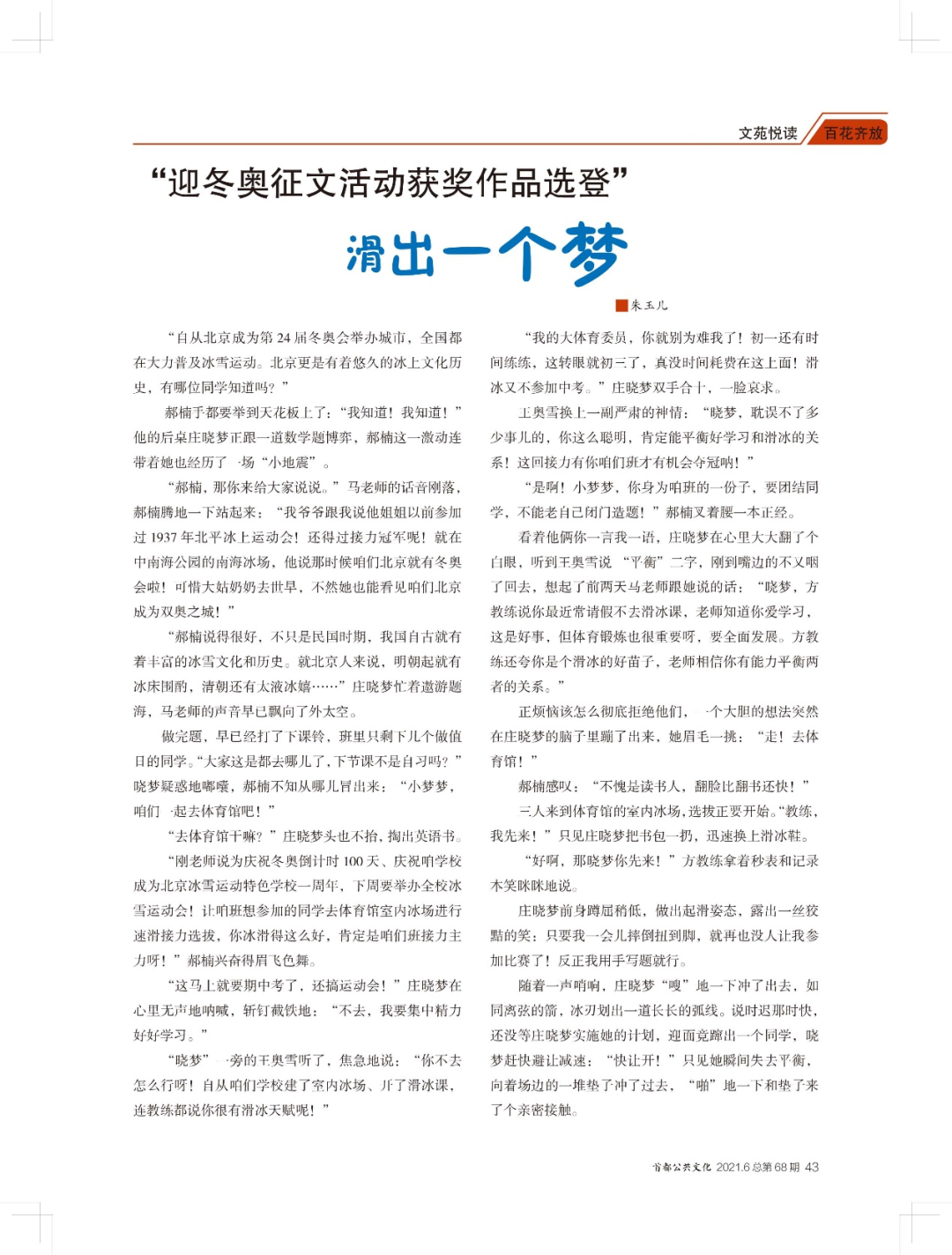
“同志,您赶紧躲开赛道,最好再多穿点衣服啊!”狡黠的话音未落,郝晴已经滑走了。
我轻轻地退出这扇门,怕惊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,看着门上2022—1的编号,难道这一扇门就代表了一期《首都公共文化》专刊吗?里面的世界,难道就是那一期专刊里刊登过的内容吗?
为了验证这个猜想,我又打开了编号为2014—6的门,只见在妙峰山香会博物馆和紫石砚博物馆里,门头沟区正在开展2014年“非遗一日游”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;同时还有从石景山区广电中心传出的朗诵声,定睛一看“我的中国梦,欢乐新北京”——第二届“放飞梦想”北京诗歌朗诵大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;打开“试刊总第11期”的门,里面一张张认真求知的面孔,原来是2013年全市文化站长培训班正在上课……
正当我沉醉在这一扇扇神奇大门背后的世界里时,一个声音叫住了我:“年轻人,参观的差不多了吧,也该回了。”我转过身,看见一位老者一袭白衣,笑眯眯地看着我。
“老人家,请问您是?”“我?”老者摸了摸他的白胡子,摆了摆手“不必纠结我是谁,我可能是一个字,也可能是一句话,就像这一扇扇门、这一个个门背后的世界,我们是你们群文人笔尖汇集起的力量,是你们书写出来的。”
“感谢您,也感谢这里的一切,是你们的存在让我有幸看到了《首都公共文化》专刊以前的样子,让我看到了群文人曾经为了文化的发展和建设而努力奋斗的身影!”
“孩子,是我们要谢谢你们啊!正是你们这一代代群文人的努力,才积累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、创造了那么多生动的形象,也正是因为你们创办了《首都公共文化》专刊,才让我们被记录下来,永远地在这个世界里鲜活如初!”老者向我轻轻作揖,转身朝着尽头的光明处走去。
“老人家!不多聊一会儿吗?”我朝着那快要与光亮融为一体的背影挥手“我还能再跟您、再跟这里的一切相见吗?”
“年轻人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好河山,别总回忆,闭眼只能凝望过去,睁眼才能预见未来!有缘,自会相见!”
缘,由我们书写睁开双眼,看着眼前未着一墨的白纸,我要拿起笔,把刚才的一切写下来,写下那位老人、写下刚才这场难忘的经历。也许因为我的书写,有一天我们还能再见,一起互相聊聊各自的世界。
此刻,我要拿起笔,写下我们群文人的梦想、写下我们群文人的赤子之心、写下我们群文人的奋斗和坚守,写下属于我们群文人闪闪发光的未来,让那个世界里永远存在、永远精彩。